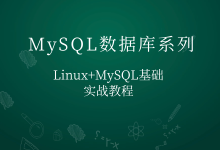假如人類沒有語言 世界會發(fā)生什么
新西蘭語言學家史蒂文羅杰菲舍爾曾指出,從所有動物語言到靈長類動物語言;從智人語言到龐大的人類語言家庭;從特定的語言到我們當前社會使用的語言,以及隨著人類開始殖民太陽系,英語在未來可能會成為太陽系語言。這是一個關于普通和獨特的故事,以自然世界中最迷人的能力為特征;這個故事是關于語言的。
人類對語言的意義有24種不同的定義。最簡單的定義是語言意味著信息交流的媒介。這個定義允許語言的概念包括面部表情、手勢、姿勢、哨聲、手勢、寫作、數(shù)學語言、編程語言等。這個定義還提到了螞蟻的化學語言和蜜蜂的舞蹈語言(我們現(xiàn)在知道,這兩種昆蟲也使用了其他的交流模式)。
語言以其多種形式在地球上進化了數(shù)億年。語言進化史和人類進化史一樣長。我們的類人猿祖先顯然有一些必要的神經(jīng)通路,可以實現(xiàn)充分信息的充分傳遞。然而,類人猿的嘴唇和舌頭缺乏協(xié)調的控制,他們無法控制呼氣。即使這些人猿能在身體上說話,他們的說話也可能與我們今天對這個詞的理解完全不同。現(xiàn)代人類大腦的體積是任何現(xiàn)存類人猿的兩到三倍,它增強了使用和進一步闡述語言的口語和推理能力。關于人類語言的歷史也是關于人類大腦及其認知能力的歷史,兩者攜手并進。
大多數(shù)專家認為,大約250萬年前,一種南方猿屬,即南非非洲人和東非非洲人的雜交產(chǎn)生了一個新的譜系,最終演變成一種人類屬和能人。能人的大腦容量高達600毫升至750毫升。相比之下,南方古猿的大腦容量為400毫升至500毫升。另一方面,能人更大的大腦允許更大、更復雜的能人群發(fā)展。只有在能人的頭骨中,才會第一次遇到布羅卡區(qū)的凸起,這是大腦中產(chǎn)生語言和手語的關鍵區(qū)域。能人可能有最基本的語言神經(jīng)通路。
然而,在這么早的時候,人類肯定缺乏證據(jù)鏈來擁有語言。在尋找人類語言的開始時,忽略了產(chǎn)生聲音和聲音所需的物理屬性。直到20世紀最后20年,科學家們才開始認真研究這個問題。似乎160萬年前,繼能人之后的原始物種仍然保留著胸椎的小孔。這個小孔的作用是讓脊髓神經(jīng)通過。它和今天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中發(fā)現(xiàn)的小洞一樣。脊髓區(qū)域的神經(jīng)控制著胸部的肌肉組織,以完成呼氣功能。有這樣一個小洞,允許通過的神經(jīng)纖維組織太少,導致產(chǎn)生聲音和聲音時所需的肌肉群控制失敗。此外,他們的喉嚨或聲音仍然像人類嬰兒一樣。他們不能在解剖學上產(chǎn)生大多數(shù)人類的聲音,直到一歲或以后的喉嚨在喉嚨里下降(類人猿的喉嚨從不下降)。早期能人頭骨的基部只有輕微的彎曲,這表明能人的喉嚨還沒有演變成現(xiàn)代成年人的喉嚨。即使神經(jīng)通路可能允許說話,他們的聲音物理器官也明顯缺乏對聲音的支持。
大約在160萬到40萬年前,除了能人之外,人類還進化出了直立人和智人。直立人的出現(xiàn)是古人類進化的重大進展。直立人比以前所有的古人都更瘦、更高、更聰明、跑得更快。從脖子到下半身,直立人與現(xiàn)代人非常相似。然而,直立的人有一個強壯的身體,頭部顯示出突出的眉毛脊柱,前額向后傾斜,大腦容量達到800毫升到1000毫升,智人達到1100毫升到1400毫升。直到最近,科學家們才認為直立人可能有說話的能力,這源于對直立人社會組織能力的認可。然而,直立人的聲音不太可能產(chǎn)生語言。脊髓神經(jīng)通過的胸椎椎體上的直立人洞仍然太小,無法控制呼氣。因此,解剖學上不可能產(chǎn)生長而復雜的詞語。15萬到10萬年前,現(xiàn)代智人出現(xiàn)在非洲,然后擴展到中東和歐洲,3萬年前取代尼安德特人,亞洲取代直立人。隨著人類的不斷進化,語言的發(fā)展和進化可以逐漸完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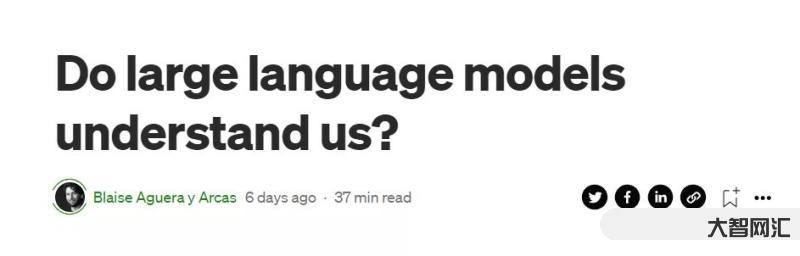
也許人們會問,為什么曾經(jīng)伴隨著我們人類進化的類人猿(包括其他動物)不能進化語言?對此,我們可以給出以下謹慎的答案。首先,猿類的大腦容量沒有得到足夠大的增加;第二,喉嚨的位置沒有因進化而下降;第三,他們的聲音器官沒有成功進化;第四,他們的胸椎孔沒有進化和擴張。另一方面,由于神經(jīng)系統(tǒng)和生理學的成功進化,智人發(fā)展了人類語言。
此外,當代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提出了一種創(chuàng)造性的觀點,即人類共享一種“通用語法”,也被稱為ug,即一組可以生成每種人類語言語法的規(guī)則。這意味著英語和莫霍克語本質上是同一種語言,除了一些不同的心理環(huán)境。傳統(tǒng)上,致力于喬姆斯基揚語言學的研究人員認為,通用語法存在于我們大腦的某些部分,這是所有人類都擁有的語言器官,但沒有其他動物。此外,人類必須在出生后的幾年內,在正常的育兒環(huán)境中,通過主動和被動的語言習得來激活這種通用語法,然后才能正常地學習語言。
支持喬姆斯基觀點的證據(jù)包括1605年由皇帝阿克巴主持的20到30個嬰兒,由沉默的保姆撫養(yǎng)長大。經(jīng)過四年的語言隔離,孩子們被發(fā)現(xiàn)沒有語言。在過去的幾十年里,意外報道的人類嬰兒在出生后被遺棄,由非人類動物撫養(yǎng)長大,然后被發(fā)現(xiàn),人類教育了幾年,但不能教他們人類的語言。與此同時,一些科學家以各種方式教育黑猩猩和其他動物,希望動物發(fā)展語言,但這些動物只能學習一些手語姿勢,或一些單詞,永遠不會組成單詞和句子,發(fā)展與人類相同的語言。
因此,我們可以說,人類語言的發(fā)展是人類自身成功進化的奇跡。
尼古拉斯斯特勒說,如果語言使我們成為人類,那么正是語言使我們成為超人。
世界上有6000多種語言。中國普通話用戶最多,超過14億,占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;其次是英語和西班牙語,約3億人。在現(xiàn)有語言中,一半的語言使用者不到500。無數(shù)語言已經(jīng)消失,許多語言正處于消失的前夕。語言社區(qū)是人類歷史發(fā)展過程中非常自然的單位。語言作為交流手段的本質,將人類分為群體。只有通過一種共同的語言,一群人才能共同行動,所以有一個共同的歷史,也使這些歷史的記憶和敘述成為可能。
語言作為人類群體的旗幟,不僅保護了我們的記憶,也是我們保存過去知識的最強大的工具。正是有了這個工具,我們才能隨時把知識傳遞給別人或下一代。相反,如果人類沒有語言,我們現(xiàn)代人類的知識體系將無法產(chǎn)生。